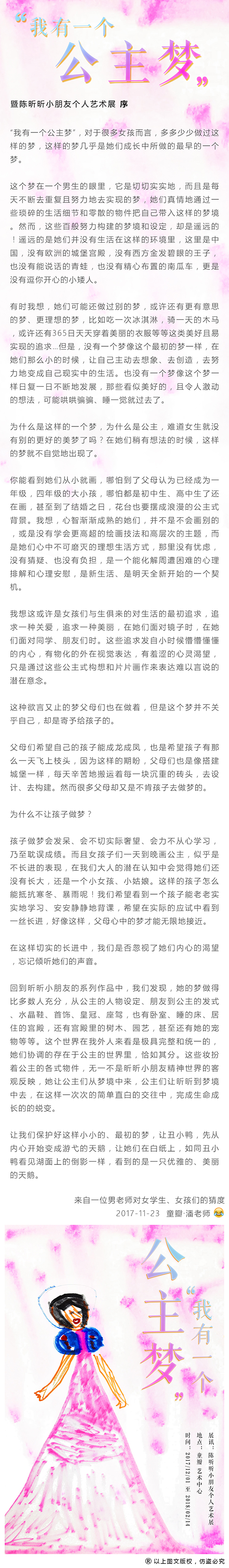一)
前两天,奶奶打电话问我:大伯家的老靠椅要不要卖?
同样的电话,我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以前,到奶奶家的时候,他还会当面和我说,谁谁谁,又想买,然后会回那人说:我阿五讲,否卖,留着他要用的。
要用?显然是不用的,至少现在用不了。我只是想象着,以后可能会用到。
就这样,又一次,电话打来,问我要不要卖?
这大靠椅子不是我的,而且和我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是哪天突然出现?也许是奶奶和我第一次说起这事的时候出现。过去我没有留意过,现在也只是徒有的关心和占念。我想留着,只是因为觉得他是旧事物,一个旧事物,对于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恐怕是失去太多珍贵的东西了,所有才这般怜惜起来,哪怕不是我的,哪怕我用不到的。
我说那就卖吧。
嗯。
那就卖吧。
卖了奶奶开心,我也清静。那人也得所需。
二)
前些日,奶奶和我说,檐门前的倒米臼被人偷走了。是晚上那些人直接开着车到家门口拉走的。
那么重被拉走了。
奶奶说:白天的时候,他们出100块问要不要卖?
这次,奶奶是不买的,虽然放在那里,不知有多少的年月,无人使用,况那臼里还积了陈年的雨水,都还长了虫子。
然而晚上却被偷偷拉走了,那么重的,竟被拉走了。
她们知道这里是老人家的住所,无人看管,所以索性就偷拉着走了。
奶奶对此却是念念不忘,如同偷了他珍贵的东西。
三)
奶奶一定不知道那些买了这些旧货的人是怎么使用的,就坐不得,也靠不得,那臼去石场新拉一个就好了。
不过,村也不是文化大村,所以,本来的就没多少旧东西,一年修条路,一年翻间屋,渐渐的,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看的、留的物件。
然后,村子却是空空的。
人也去了,物也去了。
在原本有些许纪念的地方,都日新月异了。
四)
在杭州的时候,我见了很多专卖旧事物的地方,而且分门别类的越来越细。
也有怎么用这些旧事物布置的,更多的是在茶馆、古斋、文化馆、博物馆、美院里。
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买和卖,妆点着自己的门面。仿佛有了这些物件的布置,文化和素养会不自觉地提升,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异样了。
这些物件,离开了原来出生的地方,好像也会脱胎换骨,变得清新淡雅,反而没有了旧时的味道。
城市不断现代,不断发展,而“文化人”却舍不得旧,他们舍不得自己的作品如孩子,却能轻而易举地掠夺他乡的旧物为己用,可见他们并不是真有文化的人。
做梦了,梦见两个特工样的人看守着我,也通过我的手机,监察着你。
只是你通过短信,给我发送了两个字:清空。
可还是被他们发现了。我拿着手机,看见你给我发的信息,就开始往老家的屋后跑, 路过阿太家。
阿太过逝了。屋中放着他躺着的棺材。檐门口的一帮亲朋众人在吃酒、玩乐。我慢慢地走向前,一人走到山坎边的藤椅上,静静地坐进去。我努力地想哭,却很难哭出来。他们却是说着笑着的。
又梦见到了大学,大学的一个教室那里,一个老师在说,两匹不同的马,为什么艺术的角度另一匹好看,然后说着说着,一个艺术老师却开始阐述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是表现哭的。
尤如水袋一样装着的眼泪从天上一袋一袋的掉下来,越掉越多,好像砸到了我的脸上。
终于地,我好像能哭一点了。 在朦胧梦醒之际好像感受到了眼泪的流淌。然而当我清醒之时,却没有一丝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