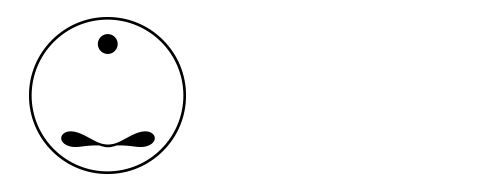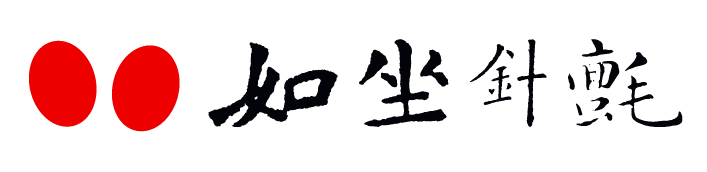一)
一条路走完
要遇到很多关口
小路有恶狗
穷追 纠缠 吠咬
完全摆脱心力也尽虚靡
大路有看守
设卡 阻拦 讨要
畅通无阻情愿总得支出
平路看似无堵
顺心 顺风 顺畅
前方卡顿不慎稍有事故
险路未知起伏
碎败 冷寂 打滑
终上垭口下坡切勿得意
一条路走完
不到终点落坐不算走完
走一条路
关口是可以预见的
即便你没有走过
至少也要个准备
除非从来不出门
还将劝诫当耳旁风
临急时可要吃大亏
绝难如若临到头上
脱层细皮已是大幸
或用血肉对赌时间
二)
有些事毕竟不可持续
但我们还将努力维持
遮遮掩掩 磨磨蹭蹭
有些事毕竟要求完结
但我们还是藕断丝连
牵肠挂肚 朝三暮四
有些事毕竟需要面对
但我们还是殚精竭虑
故作镇定 理智克服
人生有些必定的关卡
就设在那里
我们常常看不见
但它转眼又在眼前
没有一丝防备
没有一丝准备
关卡总是难过的
如果轻易过去
那也不是一座关卡
人生的关卡
虽然难过
但每个人还是过去了
三)
梦是自开的解药
在夜中时服用
梦是过关的安慰剂
抚平切不可得的痴心
梦是你我的最后一杯酒
轻轻啜饮于离别的当口
一)
夜半沥雨
在朦胧睡眼中看见了这个春天的第一记雷光
雷声没有在心中默念三秒四秒后如预期般哄响
而是又过了几秒
才闷闷地滚折过来
不惊天动地
正在熟睡中的父亲们 妻子们 儿女们 农民们
如不因这轻细的雨声而幻醒
今年的第一声雷
算是白打了
人们会在下一次更大的雷声中庆祝
在朋友圈中发图感慨
新的一年的春天到了
二)
在这第一声雷响前
或在第一声雷响后
我在梦中
因为接二连三的飞机事故
遮遮藏藏
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你
那是相似的背影
却也如过去般隐晦
直到在朋友的簇拥下
终于和你打了照面
那脸己不如我过去之所见的青春 丰满
至少也失去了笑容
那不是生活岁月留下的痕迹
那是多年不见的梦的痕迹
梦的干瘪使梦中的人干瘪
梦的无期无望让我们这次难得一见之面
也无期无望 无厢可言
你变老了
等我醒来
我意识到这绝不是你的现实之老
但那样的脸及眼色
却在我现实为你设置的影集中
深深地打印了一张
并粘放在这影集的背后
直到我无论如何翻动
终会翻到这张无趣的
与我所见所思相差极大的
瘪瘦且不甚谈笑的场面
三)
春天
应该都是一样的
每一年的春天都会有人期待
每一年的春天都会有人哀怨
只是对春之情
一年一年
换了一轮又一轮
只道今年
逢恰是我
四)
在春天老去
至少是一件幸事
至少轰轰烈烈
如若在秋
也更添悲愁
软弱无力的老人在这急速的冷却之中
甚至可能不告而别地死去
春天还有一口气
缓解了你无数的痛
百花争景像是安抚人心
体贴地轮番照应
或许在夏天还能回活过
五)
我们都老了
春天属于春天之人
网络上 有一群 85后90后up主
他们下乡了 回家了
诗画 谈琴 务田 牧畜
等等等等
曾经这一代人梦想的生活
成真了
他们用闲散而又关注的镜头
描述着零碎且又确切的角度
程序员 销售员 工程师 会计师
或者本身就带有被证明过的爱好
美院的 音乐学院的 文学院的 哲学院的
当然也有失业或从一开始就没有工作的
他们是城市里的过客
如今回来了
重新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这是朝霞与暮色的碰撞
是散文诗与族谱的对谈
而散文诗里有一些坚决的意志
族谱里却松松散散地写着惆怅
我们看着他们记录片式的影像
又听着他们认真自叙地呢喃
认真听
是孤独在那村庄里摇晃
陶渊明
应该也是孤独的
否则他也不会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我把未来的某个日子设为一个目的
就像一个锚
牵引着一艘船靠岸
到了那天那个日子
简单地做个休息
再想象着拟定下一个目的
以此反复
不断向前
促令这艰难也好激荡也好的日子
有一个确切的归宿
忽略一个人
是从忽略一个人的脸开始的
以前
你知道他今天突然哪里冒出了一颗痘
或者早上起床他上眼皮线条是否变化
又还是昨晚没睡好法令纹些显得松塌
其次是那人的手
是肉了是瘦了是否出汗了是否晒黑了
如果不定睛看或用你的手去如常感受
陌生的眼睛和初次接触的人不会体会
再者是他的穿着
花花绿绿以及衣物上的大色块是有的
但你已经很难去找出那些细节和点缀
转个头你甚至已忘了他今天穿的什么
然后是他的身形
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形
低着头在打字或干活脚跟在眼前走过
或高或矮即便他报体重也不再去说辞
当一个人被忽略或不去看
他所发生的图像便停更了
停留在了过去影像的集合
那是一个模糊且确切的脸
眼睛里有话也对着你微笑
但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细节
你很难再如画家一样添加
添加在你所得的二手资料
也很难试图设计另种造型
他始终如一地固定在那个
初次见到阳光明媚的下午
各自轻看四周而对上的脸
当时你也没有留意他脸上
是否新冒出了痘囊或皱纹
所有的记忆开始沉淀切片
归于最干净最响亮的某天
如果你再重新关注关心他
你不是像之前那样去细分
也不是像之前用手去检手
也最多稍稍留意简略地看
他今日此时与你见的装着
并问
你如何了
你如何了
你晚上回家的路可有什么变化
你所住的小区或庭院春天如何
你是否趁着这好太阳晒了被子
你家里可还收藏堆积那些空余
你新买的衣物可有没有讨点价
你这两日是否睡太迟显得松塌
你做的菜或你做的饭合人胃吗
春天
你如何了
我知道
你的答案
一个梦
大概也是可以作得深沉
像一部现实剧
当然主演还得是你和我
梦里
所有的一切也都振振有词 有依有据
简直是白日的延伸
延伸日常所不能演的
延伸日常所不能说的
延伸你我所看不见的
那常所辩驳和争论的
也是烧脑和喘息的
你我在梦里所做的一切
乃至关联人所做的一切
却竟都按着白日的结果而来
实现着本来以为可以理想的
日与夜 虚与实
真与假 梦与醒
等等幻与明的统一
那统一的不是完好无损
至少是破碎不堪
所幸
梦毕竟不如现实来得深切
在梦醒初分
可记得清晰所发生的事与人
但在彻彻底底醒后的一分钟
梦就瓦解消逝了
但它却显示地告诉我
梦里发生的及至现实这结果
你是对的
我们这样是对的
我们充分地行使了人类进化带来的理性的权力
我们并没有妄自菲薄和不切实际
我们都是现实且理智之人
我们并不依靠情感和天然的动物性来支配发生
及时斩断虚幻与可预见的贫穷
以令彼此乃至关联人与未来人
得以保全
保全各自剩余的微弱的幸
不至本来混乱不堪的命运再入歧途
当然
所有这一切
都是基于当下已成的事实
如果事实是另一番面貌
无论是梦里或日里
我们都会再去论证
证明另一种确切
但论证并不是牌局
可以不断洗牌重来
生活和梦境都仅只一条路
不断把眼前无限可能的万千
束拧成身后一个个单点及线的事与实
一)
人的最后一次离别
不隆重 且平淡
就如往常
煮碗面 放在灶头
倒杯水 放在手边
你不知道那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你不知道这是他为你做的最后一事
离别虽然平淡
天地却在打鼓
那鼓点随着远去的距离越来越激烈
他不知道那碗面是什么滋味
他不知道那杯水是什么滋味
那如往常的一碗面 一杯水
在咽下肚子后是否会翻起胃酸
令喉哑难以发出声响
直到鼓声消停
人声得以鼎沸
不告而别的人就像幽灵
人们那么形容
他来时如常人
离去却令人害怕
那消息往往不即时通知
也不当面与你陈情其中
只教人们猜想
以便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
那仅可能且确切的线索
并与之牢牢地绑定
以让天地的鼓点消逝
令生活复归平静
平静是什么
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顿饭
不声不响
二)
清明
我们都去祭祀
祭祀什么
无人得知
艳阳高照着本应绵绵惆怅的细雨天
青风吹拂
离人饭别
一杯酒
两杯酒
或许还有第三杯酒
平静的酒面
沉醉着一张愁绪停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