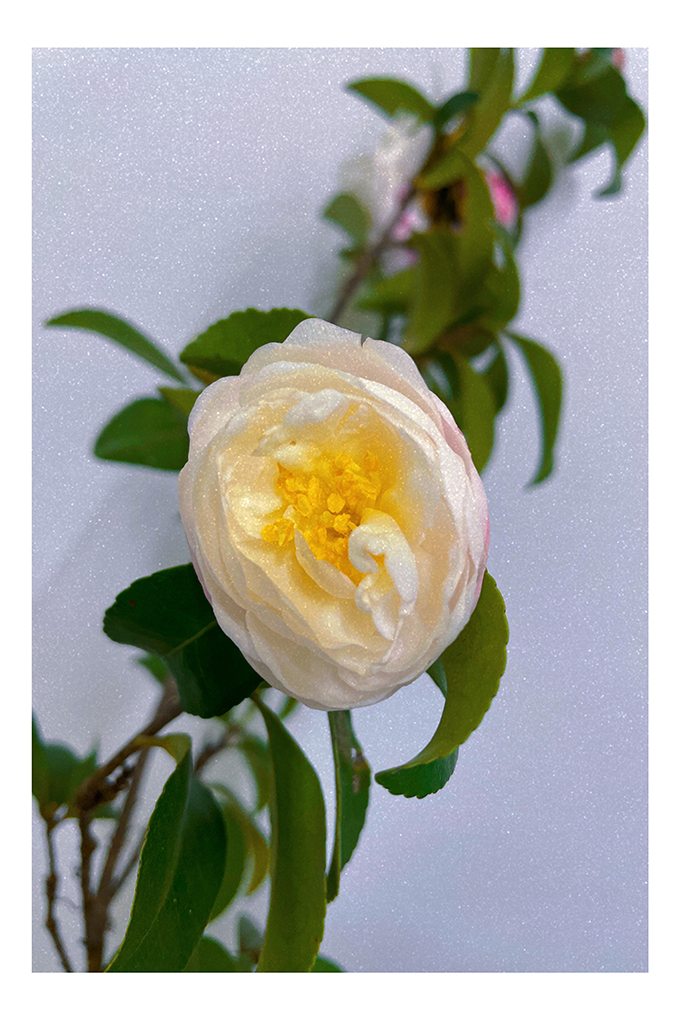病床上的女儿
病房 病人 病体
痨瘦 疼痛 疮痍
翻腾着 狞叫着
白发的母亲
赶到急喘不安的病床边
用浓密的乳汁
喂灌着近乎撕裂的女儿
满口的汁水
止息了患者焦灼的声嚷
病房 病人 病体
痨瘦 疼痛 疮痍
翻腾着 狞叫着
白发的母亲
赶到急喘不安的病床边
用浓密的乳汁
喂灌着近乎撕裂的女儿
满口的汁水
止息了患者焦灼的声嚷
我来到这里
肯定是为了遇到
一座山 一棵树 一个人
不然 以我的能力
肯定不能建立这一切
通过种种的难关
再经过稍许时日的等待
如同已经定好的期约
在此与你准时的见面
并间万众之余
一眼看到了你
一眼看中了你
美好的人不如你眼见的实在
基于过去而构建的现在与未来 不如
基于现在而构建的过去与未来
他如未然开凿的大理石
一把锤拭的斧子
即刻的美好收益于当下的细作
也凿刻出未有的实际
他的破碎 琐碎 零碎 乃至
而成的一个整体 实体
如同一座已然的雕塑
在此刻都更能约束一个人 放肆一个人
在光与火 暗与寂之契
与策千里
好好享受这平静的夜
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
在你未得到任何消息之前
所有的狂妄之灾在明天会席卷而来
此刻的风平浪静无需提心吊胆忧思忧虑
好好享受这平静的夜
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
在你未确认任何消息之前
所有的狂妄之灾若在明天席卷而来
此刻的提心吊胆忧思忧虑则白白消耗了
最后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与睡眠
好好享受这平静的夜
一)
这是为应付一次繁忙而检查的作业
前台
打扮俏丽的大波浪卷发女性拿着俫卡相机
紧张慌乱又谨慎地翻点
与我身后的男性小哥配合着我语无伦次的手
是这样吗—— 啊——是这个 ——还有这里
在每次的确定确认之下我们摊开局促的桌面
在尽可能显得大一些的镜头面前—— 咔嚓 咔嚓
经理
微微作作的强扭笑意在我们彼此流程的工作中
点头确认
经理—— 啊—— 经理
经理—— 是你啊
检查中的女性 或是在场的某个女性终于喊了
啊—— 经理你什么时候进来啦
我没戴眼镜—— 不好意思——
微微作作的强扭笑意在我们彼此流程的工作中
——我没看到你
不知何时从我们拥挤的检查工作中挤进来的
经理
他自顾自地翻检着
日期 表单 确认签名 及最底下一张
彩色的静止流溢的液体画终于又被放下
二)
被翻阅过的场地中心
一片狼藉
学员们在嘻闹
JX或JX的妹妹拉着他的妈妈在向我要兑换礼物
原本是想让他慢慢挑拣的
但突然冲进来的XM带着他洒进来的几个彩色墨点
被我寻视着过去
礼物可以下次再换或现在就随意换换
我在梦境清醒之余及时反驳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没有制度的想法
那满地的狼藉或带有肆意的墨点在有限的场地翻腾打架
我抓着他的手
凶怒地质问
你明白了没有 ——我敲打着那罐彩色喷漆
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我的怒气
他无动于衷—— 我将他拉到后门
我重重地敲打的这次 ——喷漆罐
打颤的通连向下的黑暗的楼梯不锈钢扶手
在那中间滑手跌落
我的双手牢牢地抓着他的双肩
为了让他明白我的彻底地愤怒与无尽
我的脸和我的眼
生挤着圆铮着眼
那一片的愤怒他却无动于衷地看着我
三)
你的身材很好
说明你管理得好
身材管理得好
说明你其他方面也会控制得不错
——一位做营养轻食的瘦弱而略显老态的女性推销员
她轻轻赞赏地和我说
——
你要放弃那短暂而客套的漂亮话
不要打印在心里总是回味
并把验证工作带入这荒诞的意识行为
背后黑暗的楼梯是为你隐藏的台阶
如若可以选择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