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理想
回来的路上
我看到了连绵不断的田野
傍晚四点半的夕阳
悬落在天边际
闪耀的金桔色
粼粼地点缀在时有的村院的屋顶
斜洒在一半荒芜一半欣荣的山头
没有炊烟也无晚风
但这恬静的林田处
让我想起幸福与平凡的事
幸福和平凡的事是
和你在这
耕地种田
日出日落
回来的路上
我看到了连绵不断的田野
傍晚四点半的夕阳
悬落在天边际
闪耀的金桔色
粼粼地点缀在时有的村院的屋顶
斜洒在一半荒芜一半欣荣的山头
没有炊烟也无晚风
但这恬静的林田处
让我想起幸福与平凡的事
幸福和平凡的事是
和你在这
耕地种田
日出日落
蜜蜂
飞到一户人家
红梅正放
却没有采到蜜
我最终还是压制住了
自计划与你约见之日起以来的欲望
打算孤身一人上路
那天的那夜
我并没有如往常一样的非分之想
而是颤颤噤噤
没有多余的话
不调皮 也不无助
没有怯露一丝可以用来抚慰的伤痛
紧张和不适应的南国的黑暗
把我们彻底地隔阂开
如同天堑
语言亦如断裂的桥索
你在这头看不到浓雾之中那头的桥堡
也感受到了深渊巨壑的不寒而栗
身影皮囊虽然清晰
各自的路却不再交集
天一明
我就一人上路了
从北方到南方
火车要经历数个山洞
山洞的前头 后头
烟霭薄淡的阳光洒落
笼罩着时远 时近
耳边放浪的音乐声声
是你的过去 未来
于我的眼前脑后回映
如果这车从洞影穿越
到达你的喉咙 指间
令你我发出点声响
那也不过是此时音乐下的沉默
列车
缓行 又急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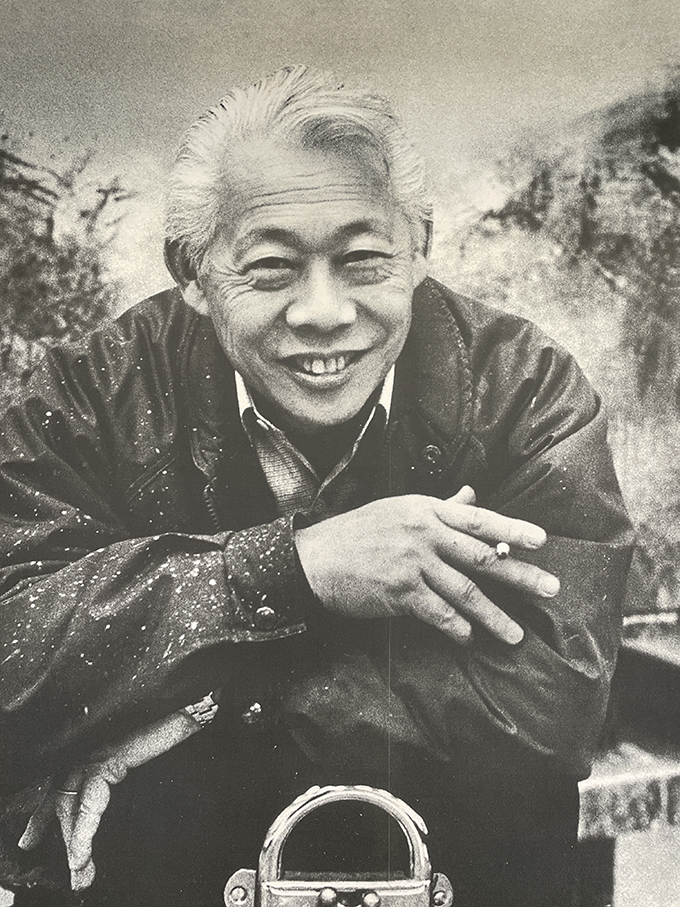
为何到了2024
仍有一种古老的情爱悲郁感萦绕在旁
宿命之缱绻 羁绊
所遇之所失 所见之所念
无故神往
一)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广告
他向所有在场的人告诉
你有还是没有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广告
他向所有在场的人告诉
你有还是没有
这是一个带凶险的广告
他向所有在场的人告诉
你有还是没有
一把尺子在心里开始衡量
你是多还是少
一套计算机在心里默默计算
你是好还是坏
手段与良知开始打架
是否需要保留或者采取行动
二)
控制的欲望
迎合的欲望
广告的欲望
在心里翻腾
一切起得太快
事后有可能幡悔
然而一旦使用过
心里便不再炎症
自然而然地
成为暴躁的人
三)
权力地暴躁
暴躁地权力
你分不清是
权力的行为 人的行为
情绪地行为 社会地行为
当一切杂糅在一个肉体上
或者选择在某一个肉体上
这便是一个行驶中的躯壳
看似在设计下的轨道之中
隐藏着随时地可以与可能
那辆高速公路上翻滚的交通事故
有时只是影响一辆或两辆
有时则是好几个小时的长龙
但高速不会停流
被清理 被疏通 被重归秩序
人们不会在路上去看 去找
曾经 过去留下的死亡痕迹
除非那是一场几分钟前的痕迹
带有血迹 气息
与一条柔软的警界线
四)
暴躁的缘由很简单
其实就是
你不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