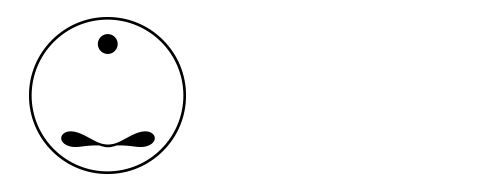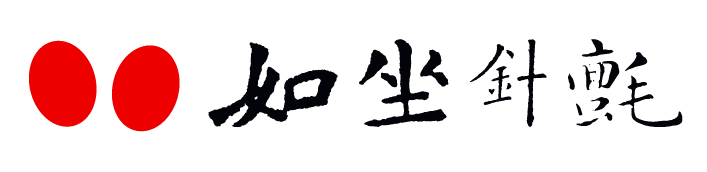一)
我们就像跑了一万米
就像跑了一万米上气接不了下气
剩下还有很长的路
总有跑不动的时候
而那个人
就站在路边
伸出手
他们都说
停下来吧 太累了
这里就是休息的地方
这条路
在跑到一百米的时候
我就说不跑了
我们跑不了那么远
你不 还要一起跑
在跑到五百米的时候
我们开始争吵
不是你快了 就是我慢了
为了同步
我们零零碎碎地吵着跑着
终于
我们不知不觉跑了近五千米
五千米
对于一个普通的女生来说
已经是体力的极限了
如果不是运动员或比赛
父母知道了也是要反对的
没事跑那么远那么久干嘛
五千米
也是你我的体力分界线
而你还是瞒着家人去跑
到了八千米的时候
我知道你累了
我也知道
我的及格线不止八千米一万米
我还得继续跑
你说送我一程
我说好
这两千米
我们终于同频了
这是美好的一段路
令人恍惚地以为这路可以持续
等我们回神的时候
已经跑出去很远很远了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跑了一万米
虽然来时的路清晰可记
虽然我们的步伐如此一致
但已经跑了很远很远了
而我的终点还遥不可及
甚至我忘记了
这最后的路
是你送我的
而我此刻才醒悟
当然地想着这路途
终于
前方路口站着一人
这里已是他的终点
你多跑的路
反而到了这个路口
父母都极力确认
就在此地了
大家都好休息
而我还得继续往前
去跑到下一个终点
二)
那个人
在这里
遇到了你
生命之幸
三)
过去
我也有很多个终点
但都执意地跑过了
而下一个终点
却不在地图上
四)
“不能再等了”
是长辈对后辈说的话
是父母对子女说的话
是我对你说的话
五)
曾经以为
“等”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我这么认为的时候
就吃了这幸福的苦头
他从来没有如实来过
等身影
等开灯
等消息
等声音
等照面
等
最是敏感
煎熬
一)
在他们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的白天乃至夜晚
在他们借以各种可能的见面机会与你深谈
表达他们对于你悬而未决之事的殷切期望
那问题与你抗争到底的冲突和矛盾的心情
化作深不可测的皱纹刻在他们隆起的眉头
及至缺乏营养而干瘪不再拥有光辉的眼球
最终通过嘴角的沉默与不自然的触动到达
隐隐悸悸且不可平息的心脏静动脉换血处
谁想最终
担心的是你
你又如此铁石心肠
也不能再用竹草追讨着你
迫使你完成那日常而应该做的事情
尊重你的选择原因不过是时间跨越的长度
在此时无力压制为轻薄的纸片供以自由折叠
如果他们管理权限级别够高且你能顺服指令
亦或是岁月早早地用足够多的次数将你磨炼
也不至于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夜中翻醒
在你终于完成最后一个安全记录的
以为可以到达目的的轮回
使你突然深切明白
所有的担心
并非凭空
二)
从明天起
珍惜每一个关心我的人
懂得 知足 报以微笑
从明天起
关心他们的顾虑与忧愁
回答他们的问题
叫他放心 不用担心
从明天起
做好自己生命理应的事
不去琢磨不确定的
那确定的它自然会来
迎接每一个朝我笑的人
像二十二岁的青春一样没有负担地回应
不板着 像过去一样活泼
不因界限与形式
不因分别而再见
珍惜现场的每一个当下
叫他放心 不用担心
一个人时
他 就是一个人
不管你
来 或不来
看 或不看
在 或不在
生活再丰富
事情再繁忙
当 一分为二时
没有等待
没有琐碎
没有日常
没有了拌嘴
因为那时
他 就是一个人
一)困惑
你不知道
一个小姑娘是否比你懂得更多
她天真无邪的笑和直白的语言
到底是打发你的幽默 还是
仅仅配合你自以为是的精深与绝伦
她所有的捧场与赞同
甚至营造的视觉意象
是安慰还是有所取获
她左手拿白纸 右手拿笔
给你画着斑斓的世界
也在纸的背面悄悄写上
她祈要的答案
而你不能解答
解答是没有答案时的游戏
答案是我们契定的无解之谜
外人的迷惑是正常的
没人像我们这样
你的解答闪烁其词
在他们那里更扑朔迷离 不可思议
你们的游戏已跨过时空的安全距离
无解之题或许应该早早跳过
而你沉溺其中
不也因自己就是无解之题本身
你所看到的配合与动作
是她原本的天性与方程
解答不是因为题目
也至少关于人
二)钦定
每个人
会回到属于她的地方
中间的停留与玩伴
在长长的生命路途中显得轻佻与假幻
所有当时以为侧重的情感与隐秘
最终变成心底飘渺的薄雾
我们迎接自己的生命之路
连亲近的家人也不能照顾
我们赶上自己的生命之路
那路上风景的星空与枫树
也仅仅是年轻的一瞬飘影
我们现在触摸的青春的手
在成为裂迹斑斑的老者之手
只有年轻与老迈相触碰才能感到震动
震动是五彩斑斓的夜与沉湎
三)像与人
多像啊
那一刻起 多像啊
身高 身型 脸型
曾经的相像只是相像
现在的相像仿佛刻在模子里
人们会找到镜中人
连排的镜子里是连排的家人
当你终于看到家人
那现实中的人就仅是过客
妹妹 弟弟 哥哥 朋友
他们也会找到家人
一代一代的家人并不在于生育的子女或更远的子嗣
在于向外看的跨越时空的镜子
有时是向上看
有时是向后看
然后相聚 相吸 相印
刻在同一个画框里
或破碎 或发黄
直到家人的离去
成为那一个孤独的你
成为那张孤独的相片
More...
我怎样才能放声痛哭
以让眼泪汹涌如海泉
淹没这世界的每一角落
沉重如躺在深水里窒息
脑海里刮起的风铃般的记忆
在此刻如峰巅的古庙响彻云底
冬天轻扫落叶将他埋入土里
来临的春天不过是轮回的泪滴
我怎样才能放声痛哭
如巫山神水汹涌奔袭
淹没沿岸的每一个角落
在事后责骂中带着悔意
告诉那善良的人他不能承受的
告诉那善良的人这荒唐和闹剧
所有的担惊和忧虑及种种不知所措
会平息
会平息
很多齿轮的旋转
有其自身的动力
小的齿轮带动大的
那是儿子带着父亲
有些齿轮大的粗的
那是公家与老板
带着小的层层转动
它们紧密相连
绞转着粘稠黑黄的机油
如皮肤上胳膊肘的污渍
时间久了
我们常以为是齿轮自己在转动
但仔细看
那不是齿轮自己想转动
齿轮的转动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空有一身的转动
它们兢兢业业地凭借自身仅有的技术
维持自己去生发那个转动的力
它们害怕随时的停歇与损毁 开裂
并在旋转的过程中
希望尽可能地将自己变大
以便在这满是油渍的绞挤的连轴的机器中
保持某种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替换的作用
齿轮的世界如此紧密关联
尽量生造出我们需要的作用
那为何旋转及初始旋转的力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
当我们面对这一轴扣着一轴的齿轮
不能让他坍塌与停歇
我们参与进去
刚开始也不过是顺带着自以为初始的力
却在这最终的配合中明白
原来每颗齿轮都如此胆战心惊
从微弱的推动的力到自动的旋转的力
到主动的转动的力到小心翼翼的跟力
生怕卡错
生怕无用
每个动物会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松鼠会上树
河狸会筑坝
旱獭会掘土
但它们不会成为老鹰遨游于天际
老鹰
目光如炬
看紧猎物一冲而下
用肥美的脂肪滋养羽毛
风雨更显其桀骜不驯的英姿
但风雨不会照顾松鼠河狸与旱獭
风雨是它们的险阻
阳光柔煦
却在阴影里伺伏杀机
为了眼下的食物
不知日复一日